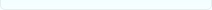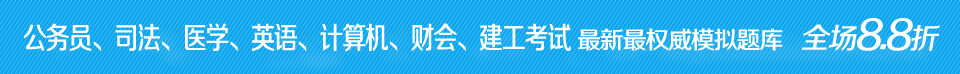劉克定
清朝的康熙皇帝很看重讀書(shū)人,致使讀書(shū)成為當(dāng)時(shí)一種時(shí)尚,形成一種“讀書(shū)熱”。不過(guò),不是所有的人實(shí)實(shí)在在讀書(shū)求知,有的人是趕時(shí)髦,甚至并不讀書(shū),出門(mén)時(shí),刻意將嘴唇涂黑,以表明自己是剛讀過(guò)書(shū),吮過(guò)筆頭,顯示自己是很風(fēng)雅的很有身份的人——這是清代讀書(shū)的“熱效應(yīng)”。
我覺(jué)得,讀書(shū)成為一種時(shí)尚并無(wú)不好,但是如果形成一種虛熱,就成為病態(tài)。中國(guó)歷來(lái)把讀書(shū)稱(chēng)之為寒、冷、苦之事。寒窗,指冷寂的讀書(shū)之地,讀書(shū)謂之“自甘寂寞”,“坐冷板凳”。甚至因讀書(shū)導(dǎo)致貧窮,那就更苦。朱買(mǎi)臣光讀書(shū)不上班,導(dǎo)致家貧,只好以砍柴為業(yè),賣(mài)柴時(shí)還手不釋卷,妻以為羞,和他離了婚。像陶淵明那樣“既耕亦已種,時(shí)還讀我書(shū)。泛覽周王傳,流觀山海圖。俯仰終宇宙,不樂(lè)復(fù)何如?”那是家境較好的人,住在田園小區(qū),悠然見(jiàn)南山,讀書(shū)打發(fā)時(shí)間,所以他覺(jué)得快樂(lè),要是換一個(gè)環(huán)境,他就不能以“羲皇上人”自居了。
奧地利作家斯蒂芬•茨威格的小說(shuō)《象棋的故事》里有個(gè)B博士,被關(guān)押在納粹集中營(yíng)里,精神備受折磨。他竟趁一次候審的機(jī)會(huì),偷來(lái)一本棋譜,悉心研讀起來(lái)。從此在象棋技藝上大獲啟發(fā),出獄后成了赫赫有名的象棋冠軍,鐵窗苦讀改變了他的一生。這是外國(guó)小說(shuō)里的故事,說(shuō)明逆境苦讀,也可以成就人才。
漢王章,長(zhǎng)安趕考,與妻共居。章病倒了,沒(méi)有被子蓋,臥牛衣中,想起自己讀一輩子書(shū),命運(yùn)不好,自料必死,與妻子泣別。人生逆境,苦不堪言。他發(fā)憤攻讀時(shí),想到總有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時(shí)候,但往往事與愿違,更不是熱一陣子的事。至于皓首窮經(jīng),更是含辛茹苦,冷寂矢志,是很高層次的閱讀,包括索引、考證、爬羅剔抉,窮究其源,常常“不知明鏡里,何處得秋霜”。說(shuō)明知識(shí)得來(lái)非一日之寒,亦非一時(shí)之熱。
當(dāng)然,讀書(shū)也有并不寒、冷、苦的時(shí)候,與苦讀相對(duì),也有“賞心悅讀”,如讀閑書(shū),讀“動(dòng)漫”,讀某名人的生活瑣事,發(fā)財(cái)指南,升官密鑰,等等,有如玩游戲機(jī),很熱門(mén),為書(shū)商所看好。但這股熱潮,不看它的飛騰花哨,只看熱潮把人推向何方,便知是否于潛心求知有益。
讀有關(guān)本業(yè)的書(shū),雖然枯燥,也“熱”不起來(lái),即使坐冷板凳,卻是花錢(qián)也要買(mǎi)來(lái)讀。行醫(yī)讀本草,攻研啃外文,“本來(lái),有關(guān)本業(yè)的東西,是無(wú)論怎樣節(jié)衣縮食也應(yīng)該購(gòu)買(mǎi)的,試看綠林強(qiáng)盜,怎樣不惜錢(qián)財(cái)以買(mǎi)盒子炮,就可知道。”(魯迅《致趙家璧》)。這樣一來(lái),自討苦吃,苦中求樂(lè),就成了中國(guó)讀書(shū)人的習(xí)慣,跟冷熱似乎毫不相干。
不妨說(shuō),讀書(shū)本身的冷熱都不是壞事,關(guān)鍵是能學(xué)到知識(shí)。人各有志,人各有求,術(shù)業(yè)有專(zhuān)攻,佛教禪宗的北漸南頓,就是講悟道的殊途而同歸。能悟道,十字街頭也好參禪,不能悟道,把經(jīng)書(shū)讀破,也不過(guò)是白讀。用功之妙,存乎一心。魯迅說(shuō)“躲進(jìn)小樓成一統(tǒng),管它冬夏與春秋”,讀書(shū)應(yīng)作如是觀,學(xué)什么,怎么學(xué),還是“各自為戰(zhàn)”,不搞“大呼隆”為好。平心靜氣,如琢如磨,如切如磋,弱水三千,取一瓢飲,然后甘苦自知,管它冷呀熱呢!只要不涂黑嘴唇故作清高便是了。